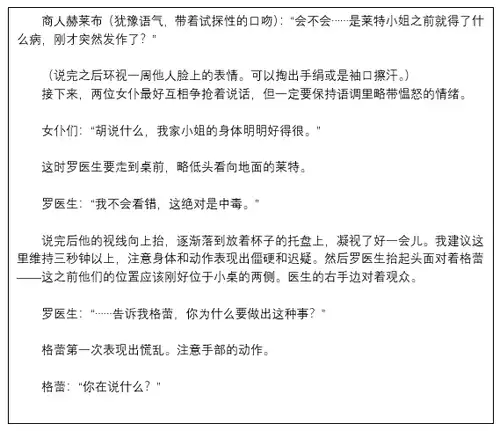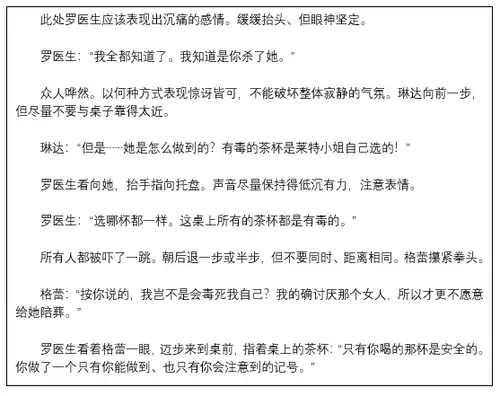古人常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样的话,也有像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样的典故存世,大概的意思都是说人世间的好运厄运皆是颇为无常的事情。但我个人却更信奉另一句话,也就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世上的好运往往难交,但厄运降临到你头上时可不会给你一点儿面子。
比如今天就是这样。对要在清早辛苦爬起来去上学的学生来说,周一这个日子已经足够晦气了,更糟糕的地方在于昨晚我为了破纪录上头打游戏打到半夜,醒来脑子昏昏沉沉的,一闭眼全是像素点。姑姑最近正颇为认真地执行着她那套以我看来不过三分钟热度的晨练计划,楼下也果然没有她的身影,但我猜测她的心情一定不怎么样。证据就是,她的厨艺一向还不错,放在桌上的早餐却实在是难以下咽。出门都快走到路口我才发现自己连衣服都没换,只好又折回去。等到我紧赶慢赶地到了学校,已经是大门行将关闭、德育老师和学生会成员纷纷掏出小本本准备记账的紧张时刻了。
尽管因为“君子协定”的原因,我不会因为迟到这种事而遭到惩罚,但在众目睽睽之下进入教室毕竟也要承担相当沉重的心理压力,所以我走得明显比平时要快。当然,校园内的变化大到哪怕是再行色匆匆的人也能注意到:原本只在图书馆的一隅暂为宣传、被艾原嗤之以鼻的那名作家的肖像被印成大大的宣传画,贴在公告栏最显眼也最亮堂的位置上;社团大楼上像拼画一样星罗棋布的招牌和横幅多数也被撤下,换上了一条带有他名字的、极尽谄媚之能事的欢迎语。事先说明,我对于这人并无情感上的好恶,以我那点儿可怜的文学水平也没法对他的作品作出任何评价;但即便是这样持着纯粹路人态度的我,走在那条“恭迎著名作家来我校莅临指导”的条幅下也不由得感到脊背一阵恶寒。最让人惊讶的是,那副已经完成的壁画消失不见了,原来的位置上只留下了刚上好还没干透的红色油漆,整面墙一片空白。我站在这既后现代又戏剧化的荒诞废墟前愣了一会儿,随后才反应过来——恐怕这上面的内容也必须要改成和那个作家有关的东西吧。
我无端联想到那种用模具培养出来的方形西瓜。
沿着沥青路向前,穿过花园,进入教学楼,我要去的教室在第四层从左开始数的第三间。这段我闭上眼睛都能走的路是如此程式化、如此具有目的性,以至于在路途中让人觉得自己不是某种碳基的、有生命的活物,而更像是某个大型机器人的一部分,一个齿轮——尤其是在有无数和你穿着同样衣服的个体在同样的轨迹上行进的时候。
还是因为路修得太长了啊。这所学校有两处大门,不论是从哪个门走到教学楼都需要五分钟以上的步行时间。清晨漫长的上学路堪比睡前的淋浴间,都是最容易让人变成哲学家的场景。毫无建设性的胡思乱想极其容易让人觉得疲惫,等终于爬上四楼之后我感觉自己的意识都有些迷离了。还好今天的第一节课是数学,那位上了年纪的老师根本不在乎课上的学生睡成什么样子,坐在最后一排掌握了地理位置优势的我那可真是得天独厚……
然后我就看到教室门口聚集了一大群人。
在走廊上围出这么一团足以阻碍交通的人群很罕见,尤其现在还是早上。有不少像我一样搞不清状况的人停下来驻足观看,隐约能听到有女孩的哭泣声。原本不愿意凑这个热闹、准备径直走进教室的我惊讶地发现引发事端的两个人自己居然都认识。生平第一次,我不顾周围人的冷眼极没礼貌地用手臂破开一条缝隙,奋力挤进风暴的中心。
正和别人对峙的巫帆怔了一下,循声望向我所在的位置。立在她对面的女孩哭的梨花带雨,双手不住地揉着眼睛——即便如此我也能认出那就是几天前来图书馆借书的女孩子。从巫帆脸上看不出任何形式的情感波动,嘴唇紧紧地抿成一条线,只有耳根稍带些红色,像是刚和人吵了一架。
我自认对眼前这个从小相识、知根知底的女孩还算是比较了解,正因为如此才会比在场的所有人都更难接受眼前的现状。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巫帆会与别人引发冲突,更不要说是比自己小一届的学妹。
……我甚至都没听过她高声说话。
印象与现实的差距带来了极大的疏离感,伴随着睡眠不足的困倦一起冲上大脑,让我有点儿恍惚。周围的视线不可避免地落到了我的身上,我能明显感觉到血液正冲上脸颊。但眼下这情况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出了什么事?”
巫帆的嘴唇动了一下,随后便转头不再看我。她的视线放得很低,我一度以为她不会回答我的问题了。
“……只是我们社团内部的一些……事情。我们……我决定把那个剧本撤下来,不会在艺术节上参演了。”
女孩用最平静的语气说出了最令人难以置信的话。有一瞬间我都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了。
“……为什么?”
“已经是决定好的事情了。”
巫帆说这话的时候直直地望着对面的女孩,话的内容也更像是冲着她而非冲着我。女孩睁着盈满泪水的双眼愣了一会儿,旋即便捂着嘴巴跑开了。人群自动为她让出一条道路,我抬起手臂却根本不知该如何挽留。巫帆仍旧挺着胸脯立在原地,手指绞在一起。我吐了口气,转身走到巫帆面前。
“我和你说过有事可以找我商量。”
巫帆移开视线:“我也没遇到需要你帮忙的事情。”
“没闹这么大的话我说不定就信了。”
女孩抬起头看着我。她抱着胳膊朝后退了一步,身子都快贴到墙上了。
“那也只是我参与的社团内部发生的矛盾而已,说穿了就是我个人的私事。我没有把事情告知你的必要,你大概也没有在我面前咄咄逼人、追问个不休的立场吧。”
……也是啊。
我感到一阵近似悲哀的沮丧。不仅是源于自己的无能,更多的是因为自己居然逼着她说出了这种根本不像是她会说的话。
“你说的对,是我唐突了。对不起。”
巫帆的睫毛颤抖了一下,身体似乎缩得更小了,上身却依然直直地挺着。四周的看客越围越多,有些人甚至开始交头接耳,事到如今我已完全不知该如何收场。
“嚯,这么大一群人啊。是不是都嫌自己德育分太多了、急着想被记过是吧?”
班任不知何时出现在人群外围,用老师对学生的那种特有的洪亮腔调吼出这句听着像调侃实则明显是威胁的话。原本堵得像围墙一样的众人顷刻便作鸟兽散,有两个莽撞的家伙差点扑到了我的怀里。
——救世主偶尔也会穿高跟鞋啊。
女人端着胳膊默默地看着眼前这些学生跑光,随后又走到门口将教室里那几个探头出来看热闹的人像敲地鼠一样赶了回去,这才来到我和巫帆面前。她先是打量了一下我俩脸上的表情,随后便一如既往地摆出那副看着像是不怀好意的微笑。
“具体什么事儿我也就不问了。是你们两个人的话情况反而简单了,什么都懂,我也就不再多费口舌。就一个要求:尽量别给我添麻烦。今早这事儿好歹是给我先发现了,要是给那些专门抓小辫子的看到了,不得连着我一起到教导主任那儿参上一本?听那老头儿喋喋不休地训个半天可没劲透了,你们也得为我考虑考虑不是。”
巫帆机械的点着头,我则一声不吭。女人盯着她看了一会儿,忽然松了口气。
“算啦,别在这儿杵着了,都回去吧。对了,巫帆啊,”女人突然停住脚,“徐老师让你尽快去她那儿一趟。我先给你打好预防针,戏剧部的事情让她这个指导老师非常生气。”
女孩垂下头:“嗯,我知道了。”
“那就好,反正我是把话带到了。噢,还有,”女人偏过头冲我挤挤眼睛,“别的事儿我也没忘,等有时间会找你算总账的。现在暂且先记着吧。”
我毫无反应地从她身边经过,进入教室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不是因为我不相信她的威胁、事到如今还心存侥幸她会对自己网开一面。
——而是来自班主任的所谓惩罚,在现今的情况下真的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
大概初中那会儿吧,我看过一部由知名推理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剧中的主人公是大学物理系的副教授,在已经掌握了所有事实、准备揭开案件真相之前的那一刻,他总是会掏出马克笔、粉笔或者因地制宜地捡起树枝和石子,俯身在目之所及离己最近的平面上默写上一整面的物理公式。配上背景乐里极为带感的电吉他旋律和演员本人俊朗的面容,整个场景尽管看着有点儿荒诞,但更多还是带给观众一种高深莫测的潇洒感。根据剧中角色的自述,这样做有助于他厘清思路、更快得出正确的结论。
我是文科生,自然也就无法测试这一方法的可靠性,毕竟过去学的那点儿物理基本已经原封不动地还给老师了。但我能为之作证的是,数学公式对于理清逻辑是一点儿帮助都没有。这里必须要感谢一下我们五十多岁的数学老师不辞辛劳地写了那么久的板书,但我盯着那一黑板的导数公式看了四十多分钟,脑子里仍旧是一团乱麻毫无头绪。可能是因为课上教的这些还不够深入吧——和艾原平日里给我单方面灌输的那些不定积分线性变换之类的、天书一样的东西相比,黑板上的这些式子起码还属于正常人能看得懂的范畴。
……只不过对我的思考毫无帮助。
下课铃响了。还在黑板上奋笔疾书的老师愣了一下,慢慢转过身望着我们,似乎没想到往常和一整个世纪差不多难熬的数学课今天居然会结束得这么早。他推了下眼镜,用极低的声音说了声“下课”,随后便夹着教案离开了——就好像是在害怕把伏桌沉睡的那些学生给吵醒了一样。清晨的瞌睡虫似乎更难战胜,绝大部分人还都趴在课桌上。我也俯下身把头贴近臂弯里,但拜早上的插曲所赐,困意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喂。”
有人敲了下我的胳膊。因为是熟悉的声音,我并没有理会。
“喂!别装死了,快起来。知道你没睡。”
我懒洋洋地调整了一下姿势:“明明知道别人有正经的名字,却只用语气叹词来称呼,这不管放到哪儿都是极为不礼貌的行为吧。”
下一秒钟,我就被人揪着衣领拽了起来,视线对上了一张气鼓鼓的脸。宫羽华左手叉腰,右手提着我的后脖颈,一副有什么东西郁结于心却又不得不发的样子——像是在超市大酬宾开始前被拦在门口的主妇,或者是刚踏入自助餐店、正准备要吃下一整头牛的食客那样。
“跟我来。”
她只简单地说了三个字。
在一所公立普通高中里四处探险并非多么吸引人的事情,尤其是在仅仅十分钟的课间休息时间里。好在宫羽华要带我去的也不是什么偏远的秘密教室之类的地方,而只是楼下的自动贩卖机。她从机器里按了两瓶罐装咖啡下来,我想掏钱却被摆手制止了。
“算姐请你的。”
乐得从命的我坐到路对面的长椅上,霍地一声拉开拉环。宫羽华挨着我坐下,心不在焉地把玩着手里的饮料罐。
“巫帆那件事,你想明白了吗?”
女孩开门见山。我啜饮了一口罐里的咖啡。味道还凑合,只是对于正经的咖啡来说这口味还是太甜了。
“你不是也听到她是怎么说的了嘛。那是人家自己的事情,我哪儿来的资格去指手画脚。”
身边的女生一下子站了起来:“我说你是不是傻了,连违心的话都听不出来?因为别人一时上头说的气话就耍脾气闹别扭,我真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小肚鸡肠的人。”
我看着她气鼓鼓的脸颊,疲倦地吐了口气。
“我当然知道她心里不是她嘴上说的那个意思。巫帆不是会被情绪推着走的人,不可能凭着一时冲动就说出会让自己后悔的话。她不惜冒着刺伤我的风险也要把话说出口,一定有她的目的。“
“那——“
我用眼神示意她坐下来。宫羽华目不转睛地望着我,我仰脖将罐子里的饮料喝干。
“怎么解释呢……今早的巫帆给我一种感觉:她不是不情愿让我帮忙,反而更像是害怕我真的会解决她面临的问题,才会从一开始就质疑我插手的立场。所以你问我会不会因为巫帆说的话而不高兴,那没有;但是不是因为没法对现状做出任何改变而感到沮丧,肯定。”
我抬手把饮料罐扔进不远处的敞口垃圾桶。宫羽化的视线跟随着那东西在空中划过的弧线,而后“呼”地叹了一声。
“你还记得那天吗。下雨,我们几个都在图书馆。”
“嗯。”我回到椅子上。
“那之后我就跟着巫帆去社团开了会,讨论艺术节上要演的剧本。之前大家一致同意要排那个《雷雨》,不少人原著都读过好几遍了,演起来得心应手。但郁兰——也就是你早上看见的那个妹妹、我们社团里负责写剧本的——一直坚持说要写一个原创的推理故事。大家拗不过她,最后也就同意了。”
我望向前方:“听起来其他人好像都不太信任她。”
“……多少有点儿吧。其一是,我们之前演过的两个本子都改编自名著,还没尝试过原创;其二是,至少我觉得,她……”
“她并不是特别了解推理。”
“……嗯。虽然我也不太懂什么推理啊悬疑之类的,但我知道这些都是很复杂、很费脑子的东西,得那些特聪明的人才能搞明白。郁兰是个勤奋的好孩子,可她平时看着根本不像是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的样子。我们都觉得她是被那个讲座上的作家给洗脑了,才会这么执着于推出和推理有关的剧本。”
怪不得当时会一次性借走那么多推理小说啊……现在看来应该是当成考前恶补的资料了。先不论这一做法的效果如何,那女孩肯定也是拿出了认真的态度去对待,要说是一时兴起也未免有失偏颇了。
我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肩膀。从出厂以来十几年间从未上过润滑油的脖颈发出令人不悦的喀啪声。
“然后呢。特意把我叫出来,接着还告诉我这些,你心里一定有自己的猜想了吧。”
宫羽华瞪着我,随后翻了下白眼。
“你知道吗,有时候你这种就很让人讨厌。”
我不知道她所说的“这种”指的是什么,只能无辜地耸耸肩。好在她看起来只是不想放过任何一个数落我的机会罢了,很快便回归了正题。
“事先说好,我不觉得我想的就百分之百是对的,只是早上一看到她们吵起来就回想起了之前发生的事情。她们两个估计是因为剧本的长度起了冲突。”
说到这儿宫羽华抬起头,像是在揣摩我脸上的表情变化。
“周六的排练你不是也来了吗,剧本在前一天的下午才完成。我也说了,我对推理这些一窍不通,没法评判故事写的好还是不好,在我看来至少还挺热闹的。但剧本整体上有一个没法忽略的问题,那就是太长了。”
“是因为时间有限台词记不过来还是……”
“也有那方面的原因吧。”宫羽华笑笑,“毕竟不到五天的练习时间真的不够用。但更主要的麻烦出在演出时长上。按艺术节的规定,单项节目的演出时间上限也就是三十分钟,而按照原本的剧本设定排完绝对会超过一小时。”
啊……
“于是在那天的讨论会上,经过大家的一致同意,剧本被砍掉了百分之四十的长度,我们试演时候排的也就是精简后的剧本。但就是现在的这个本子,演完前四幕时间也超过了半小时,根本没有给结局留出时间,势必还要再次删改。那就……”
宫羽华欲言又止。
拿出任一领域作为参考系,我都算不上有半点才能,更遑论成为某种形式的创作者了,难以设身处地地代入女孩的心境。但只是泛泛地设想下自己投入心血和努力的成果竟然要因为这种理由就要被删减的面目全非,大概谁心里都不会好受吧。
“那剧本目前的情节已经很跳跃了。”
“还不止这样呢。”宫羽华的声调颇为低沉,“还得把立定跳改成三级跳才能符合要求。我也不理解巫帆为什么这么匆忙地下了决定——按道理这么大的事起码该和大家商量一下的。昨天下午她突然在群里发了一条消息说要弃演,之后就再没信儿了。现在部里的其他人应该比我还懵吧。”
我对相关的规定一无所知,但退演应该不是比如举手站起来说句‘我要取消演出!’就能轻松地全身而退这么简单的吧。我将想法告诉宫羽华之后,女孩不由得露出苦笑。
“想的倒美。先不说学校层面的问责,所属社团的指导老师第一个就不答应。不过看巫帆那样儿,估计她想自己一个人全部扛下来。”
“那她会怎么样。”
“能怎么样。”宫羽华摊开手,修长的手指像有弹性的枝条一样上下晃了晃,“大不了就是被老师从社团除名呗,反正到下半年也要自动隐退了。她肯定早就做好了要离开的心理准备,只是不能接受这种离开的方式吧——让一个没完成的企划成为自己在社团里做的最后一件事。”
可能因为起风了,她忽然扣上了兜帽,抱着双腿缩成一团。
“……我也不能接受。”
我看着那微微颤动的帽顶,轻轻咬了咬嘴唇。
“所以你觉得巫帆和那女孩是出于被迫要对剧本进行删改的原因就起了争执?”
尖尖的兜帽顶朝下一沉。我叹了口气。
“决定是大家一起做的吧,多少也有点迫不得已的意思。我不觉得那女孩是不明事理的人,说她因为这点就把罪责一股脑记在巫帆头上,这未免也太牵强了。”
“所以我才说那只是‘我个人的猜测’而已啊。”宫羽华一下子掀起脑袋,“反正我知道的已经全都告诉你了,要怎么做就看你自己了。”
“……恐怕巫帆并不希望我真的做什么。”
“管她怎么想的干嘛,想想自己要怎么做才是关键。一个大男人做事怎么这么瞻前顾后的。”
女孩说着,起身拍拍裤子上的灰尘,将手里那罐没开封的咖啡塞进我的口袋。在她蹦跳着跑上门前的台阶之前,我开口提了个小要求。
“给我看看你手里的剧本。”
对事物所怀着的执念几乎是最累人的情绪了,哪怕是在旁观者看来。
你可能对什么东西废寝忘食呕心沥血地付出一切,但最后做出评判、把握生杀大权的人可能一点儿也不关心——甚至根本不晓得这东西是什么。比起在乎自己“要以何种方式离开”这种事情,从一开始必须要离开的这个决定就有很大问题。
……不过说到底我也不是当事人啊。
我拉开椅子坐到柜台后面,从包里掏出宫羽华借给我的剧本。她把这东西丢进我书包之后没说上几句就匆忙跑去训练了。这几天她一直跟在戏剧部这边,其实下个月就要参加全市高中联赛的篮球队催得更紧。和她差不多时间离开的还有巫帆——这是我近两年以来第一次看到她早退。下课铃响过之后她和老师打了个招呼,随后便背起书包无声无息地从后门走掉了。我看着斜前方空荡荡的座位,忽然感觉静不下心。
于是我也溜出来了。
多数人还在上最后那两节课,阅览室里空无一人。我拉上身后的窗帘,开始阅读这本我已经看过的话剧。
首先让我觉得惊讶的就是剧本的细致程度。从字体能看出这是手写稿的影印版,上面密密麻麻地画着删除符号和划掉用的横线。依照这份原版的剧本,整部剧足足有七幕,前面用了很长的篇幅来介绍出场人物的恩怨,只停留在背景介绍或者是人物叙述里的事件按原案其实应该是发生在舞台上的。后面的剧情主干也有不少的删改,比如原文里的那三组人都是处在各自独立的场景,而出演时则大概是出于现实道具方面可行性的考虑,把他们整合在了一个大场景里。最明显的是在对演出细节的描绘上,几乎每句台词之间都夹杂着大段的心理介绍和动作描写,巨细靡遗到不仅介绍了演员的站位和动作,甚至不厌其烦地嘱咐了当时该采取的视线方向和表情。演员们普遍僵硬如木偶般的表演实在是怨不到他们,因为剧本真的没给他们留下太多的发挥空间。
我没写过任何形式的东西,自然对创作的具体过程不甚了解,但即便是以旁观者的角度看这种程度的写作也是相当耗费脑细胞的。之前对剧本作者是否遵循了逻辑性的担忧完全是在杞人忧天,剧中所描写每一个场景显然都经过了仔细地推敲。其实在翻开剧本之前,我就知道毛病一定出在故事的结局上。前面的部分已然经过了试演的测试,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应该当下就发现了。虽然整体的效果不算理想,但看上去还不至于存在让剧本直接腰斩的大漏洞。基于此,我对那没有上映的第五幕更感兴趣了。
剧本并没有多厚,从前面翻也很容易就能找到开始的那页。这一幕的情节紧接上一幕的末尾,众人在短暂的犹豫之后立刻将怀疑目标锁定在格蕾身上,异口同声地指责她是事先在饮料里投了毒。但格蕾抵死咬住一点不放:自己自始至终没有碰触过被害人手里的茶杯,而那只杯子是被害人自己选的。如果是无差别地在所有茶杯里都投了毒,那就没法解释同样喝了茶的她却毫发无伤这件事。无法解释这点的众人又将目光转到另外两个嫌疑人身上,但最终两人以一种在我看来很没有意思、却也理所应当的方式排除了嫌疑——他们的身上并没有携带毒药。案件一时陷入僵局,众人都沉默不语。 接下来的部分,我觉得直接援引原文可能更方便些。
——所以果然是杯子的问题。我回想起在巫帆拆箱时看到的那个单独包装的茶杯。但……我不知道。
这是个颇为古典的故事,大家从一开始就知道是谁犯了案——或者说谁最有嫌疑,只是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也因此,剧中并未出现专职的侦探角色,结论是由唯一的专业技术人员罗医生得出的。纯粹从诡计设计的角度看,对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推理作品的新手而言这样的想法堪称精妙。
唯一的不妥之处在于,这和我曾经看过的一本小说里出现的桥段几乎一模一样。
我盯着桌上的剧本看了一会儿,朝前拖拖椅子,打开桌上的电脑。老掉牙的机器发出刺耳的轰鸣声,硬盘唧唧直叫。
我想找来作对比的那本书早在半个月之前就被借走了,而且到现在还没还回来。
来回确认过十几次之后,我丢开鼠标,重新将视线转回到面前的剧本上,百无聊赖地翻动着。
剧本的扉页上写着“暂定”标题以及演出人员表,角色大概是按照出场戏份的多寡排列的吧,格蕾的名字排在最上面。演员名与角色名一一对应,只有格蕾和莱特后面的出演人员名字遭到过涂改,留下两块颇为纠结的黑斑。话说,那些女仆居然也有正式的名字啊,比如其中一个女仆就叫珂赛特,看起来比主角的名字都用心多了,只是剧里从来就没出现过。可能那个叫郁兰的女孩儿和我一样不擅长起名字……
长长地吐出一口气之后,我将剧本远远地推到一边。这种没法确认疑点的温吞感真让人不舒服。虽然凭记忆推断也算大差不差,但那毕竟不是靠谱的实证。
——记得西门外面好像有家旧书店。
我讶异于自己在这件事上的行动力。几乎是在冒出这个念头的同时,我起身把剧本塞进包里,锁上阅览室的门,下楼朝校门口走去。